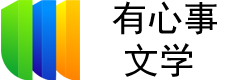今天是凌晨的飞机,我没什么要带的东西,就给古阳发了条消息,然后带上行李去了机场。盐璃岛的飞机场不大,每天固定只有三班,我选择了凌晨登机,人少没有撞人的风险。全程都很顺利,我戴着眼镜被空姐带上飞机,安稳地在位置上放松下来,飞机没有晚点顺利起飞,久违地在飞机睡了一觉。飞机穿过高高的云层,我把眼镜拿在手里,静静地看着外面,云层里甚至能看见阳光,阳光也是朦胧的样子,整个天空都像个巨大的棉花糖,我举起相机打算拍点什么。“亲爱的女士们,先生们,本次航班已经到站……”机械的提示音响起,我快速戴上眼镜,起身去拿箱子,箱子里的东西很杂,我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拖动着。“我帮你拿下来吧,你一个人女孩子不太好拿。”鬼使神差的一切,我又听到了那个无比熟悉的声音,和昨晚上一样,和那个人也一模一样。我还没来及拒绝,行李箱被拿了下来。“谢谢你啊。”我诚恳地道谢,然后抬头彻底呆住。那个声音不是很像那个人,而是在平平无奇的某一个清晨,我再次遇见了那个人,我的许柯。我整个人都开始轻微的颤抖,我努力张了张嘴,嗓子哑的什么都说不出来,眼睛隐隐传来痛感,我低下头取下眼镜,一字一句地开口:“谢谢。”声音沙哑也不好听,我无意识地抠着手心,手心里留下指甲印。许柯也像如梦初醒般询问我:“不如我帮你拿下去吧,感觉你状态不是很好。”我强迫自己抬起头看他,执拗地摇头,然后再次道谢离开。“她的眼睛还是好漂亮啊。”许柯喃喃道,那双眼睛如此漂亮只是太过平静,远远地望过去像一潭湖水。我眼前一下子模糊起来,我从他手里接过行李箱急匆匆地往外走。里港的机场很大,吵吵嚷嚷的,我攥着行李箱把手,手上已经有明显的红痕,其他地方也开始一点点变白,我冷静下来,拨通电话问:“你在哪儿?”“A出口,黑色SUV。”古阳回答的很简洁,我问了工作人员,往A出口走去。刚走出就看到古阳懒洋洋地靠着车门,冲我挥了挥手。古阳换了一个发色,蓝黑色的头发加上一张白皙精致的脸,配上右耳上单独黑色耳钉,浅粉色的外衣配上白色工装裤,阳光下非常吸睛。我走过去把行李箱拿给他,熟练地开门坐上后座。“不急着走,我还得接个人。”古阳放好行李箱,接着盯着出口。我闭着眼睛休息,不忘怼一句:“战队不景气打算开滴滴啦?”古阳无语翻了个白眼。不一会儿有人拉开副驾驶坐了进来。我鬼使神差地睁开眼再次看见许柯,不可置信地看了几眼,许柯看着我笑了笑打招呼:“又见面了。”我点头算是回应,接着闭着眼睛休息。“给你介绍一下,这是我发小兼合伙人,她也刚回来还没缓过劲。”古阳的声音传过来,我没动打算装听不到。车里空调开的很低,我动了动脖子,打算起来找个毯子盖上。“我把温度往上调了调,毯子在你右手边需要我帮你拿吗?”许柯的询问声很温柔,我没反应过来,只能机械地点头说谢谢。古阳往后面看了一眼,笑的意味深长,问许柯:“你今天格外反常哦~朋友。”许柯从他们俩认识开始,身边追他的就没断过,性感的可爱的知性的,各种类型几乎都有过。追他的方式也五花八门的,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,无人成功渐渐也就无人挑战了。他呢,对谁都是淡淡的,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,难得今天那么积极。我望着窗外面发呆,熟悉的里港市人民医院,我盯着牌子发呆,古阳从后视镜里看到,想起什么似的开口:“这个是新修的院区,原来的那个院区成儿科专属院区了。”我点点头,模模糊糊地想起自己很多关于医院的记忆,我想了想开口说:“我前几天去医院复查,路过胃镜肠镜区,我看了会儿发现胰腺癌的致死率已经是癌症前三名,病房里还是有很多疼得下不了床的老爷爷。”我闭上眼睛回忆,“所以那个老头儿应该不会怪我了吧,他当年多疼啊,我怎么舍得不让他走。”许柯的记忆突然开始复苏,他回头看向养神的少女,岁月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,除了身上的忧伤越来越浓。他突然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,他跟着老师后面查房,那个在病房里低头练字的少女,不管什么时候都像是一株植物,安安静静地慢慢生长,她好像很少崩溃很少哭,就连她小姨哭的歇斯底里的时候她也这样默默的,能想起来的只有那天的混乱。还有易斐的那句:“小姨,外公疼。我们让他走吧。”那天的易斐和许柯同样痛苦,两个人一起躲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大人吵架。“你们说的轻巧,治病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?什么叫做我就等着爸爸走了霸占他的财产?!”易殊吼了一句,她的声音被很多声音压着,听起来模模糊糊的,人声停了一瞬间又叽叽喳喳地响起来。今天早晨易爷爷在睡梦中走了,病房的人就一下子多起来了,吵吵嚷嚷的。易斐和她小姨抱着哭,哭着哭着小姨拍了拍易斐,跟易斐说还有“恶仗”要打,易斐一知半解地点点头被许柯带走。其实易爷爷去世的时候的样子很安详,睡颜几乎和原来没有区别,活着的时候就觉得葬礼没必要办的太大,没有必要做给别人看,易斐小姨支持他所以早早地选了地方。可是易爷爷的家族很大,分支也很多,连名字都不叫出来的人太多了,易斐跑的更远了。这场闹剧发生的很突然,那些没有见过的脸进来就开始指指点点,一直在和易小姨争吵,嘴里都是遗产房子…易斐整个人愣在原地一直扣手,我怕她们出事,但是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,只能伸手去抓,但是什么都抓不到,那种无力感太熟悉了,也是我的很多年之前。“谢谢啊,麻烦你带衣衣走。”易小姨用口型告诉我。她的声音又陡然提高:“你们都不想想衣衣吗?我姐和姐夫走的那么早,现在爸爸又去世了,衣衣还在上学而且她的病也一直没有治好,以后用钱的地方还不知道有多少,遗产可以分,那带衣衣的责任我们也可以分。”一下子目光都到了易斐的身上,人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。“她这个病都花了那么多钱,还是没治好啊?!”“可不是嘛,这么多年我都没听她说几句话,以后多半也是个傻子。”“老的走了还留下个小拖油瓶。可怜喔~”“今天自己亲外公死了也不哭,真的是个白眼狼。”“易老爷子这辈子也可怜,女儿女婿没有了,还留下个有病的女儿。”那些声音窸窸窣窣,我听的全身都在发抖,刚好床头还有一杯豆浆,我抓着就往人群里砸,大声吼:“够了,这里是医院,不是菜市场!闲杂人等都出去,我要叫保安了。”人群一下子散开,住院部的医生喊来了保安,这场闹剧终于消停下来。易小姨去办出院手续,顺便订白事要用的东西,这些我都不懂去了也没用。我坐在病床前发呆,看着空空的病床发呆,想着小老头平时被我气的吹胡子瞪眼,他原来生气的时候是哪只眼睛先瞪我来着,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出去一趟给易斐带了饭,易斐吃了几口又坐在病床前发呆,我从兜里掏出来几颗糖,安慰道:“带我的老师常说生老病死命运轮回,让我看的淡一点,就不至于那么痛苦。”易斐抬头看我,日常交流对她而言还是很困难,她张了张口什么都没说,只是看着我。我早早地就知道了她的不一样,她的病听小姨说也是很小的时候就有了,某一天之后就像这样再也不能和陌生人说话,这些年的康复治疗也做了很多。我又说:“我来这儿实习的第一个星期就送走了一位奶奶,她每天都很配合我治疗,我做什么她都鼓励我,说没事慢慢来,但是她来的太晚了不出一个星期她就走了。第二个就是你外公,他也算是我亲手送走的,你小姨和外公也很好一直很照顾我。所以,我们都要向前看,尽管我们都无法释怀。”我的声音断断续续,带着哭腔说话也黏糊糊的。她那天拍了拍我,把刚剥好的糖递给我,应该是组织了很久的语言,说出来还是磕磕巴巴:“哥哥,你不要难过,我外公走之前说如果我们在这边哭的太厉害,他在那边的路上就会下雨,他没有拿伞会被雨淋湿的。”我愣住,把糖放进嘴里,甜味弥漫在唇齿间他冷静了下来。我站起身整理了衣服,絮絮叨叨地给她交代,让她别乱跑等会儿小姨就来接你,实在想睡觉的话就来值班室找我,饿了的话也来值班室找我。“衣衣,跟我说句再见吧。”我嘴唇动了动,我又说:“算了医院实在不适合再见,那就跟我说……”他说话很快,她很认真地听,理清楚后点了点头说:“再见,哥哥。”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出病房门,也拿走了门口的编号。不一会儿,小姨就回来了。她收拾好了东西,给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带了水果,又腾出了一只手她拉着我,和我说谢谢,我摇头。易小姨紧紧地牵着易斐,她们把水果带给护士站的医生和护士们,一步一步地走出医院。那年的易斐不过是初中的年纪,脸上还有稚气甚至有婴儿肥,还绑着马尾,易斐的眼睛带着对世界的探究和好奇很灵动的一双眼睛。人和人之间相遇的第一面往往就奠定了往后的故事走向,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,许柯站在原地看着易斐离开,反反复复。
小说《坏掉的夏天》试读结束,继续阅读请看下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