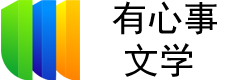姜顺儿手忙脚乱把小侯爷扶上座,对面明艳美人也跟来娇滴滴地坐下,有一搭没一搭地薅着老母鸡的毛。赵枫岚抚着通通跳的心口,一直到门童把礼单念完,才好算找到了真实感。仙人刚才的出场太过惊人,小侯爷怕自己只是做了个梦,一不小心就碰碎了。可仙人不光没有乘着云彩飘走,还陪着坐下了。不光坐下了,仙人还和他同喝一壶茶。赵枫岚的面上悄然一红,绯色都快漫到耳朵尖儿了。姜顺儿跟在一边站着,几次用眼神示意小侯爷都没有动静。没有办法,只好自己硬着头皮顶上前,“小的与主子不过一个来征税的小官,在此谢过阁主亲自迎接了。”美人笑着点头,姜顺儿就顺着向下夸起来,“没想到这小小的胶台,竟还藏着阁主这般天仙样貌的女子,宛如明珠灿灿生辉,在下真是……”姜顺儿是谁啊,他可是从小给小侯爷打小抄打到大的第一伴读,知道小侯爷已经痴了,顺杆夸起美人那就是卸了闸的洪水,引经据典,摘词颂诗,赵枫岚听得晕晕乎乎只知道在一边点头傻笑。没等姜顺儿说完,美人已经抬起了纤纤玉手,示意不用多言。衣袖滑落漏出一段藕臂,几只造型精美的金镯相互碰触,发出悦耳声响。美人丹唇微启,“我什么时候……”赵枫岚的心就像小鸟一样神游天外,他都想到了等和美人成亲后,要一对龙凤胎,眼睛大大的,鼻头尖尖的,嘴唇红润润的,一定像极了美人。娘,见信平安,枫岚一路征税,遇到了顶漂亮顶温柔的贵人小姐,列祖列宗保佑,定要求之……就在这时,他听见一道声音,“我什么时候,成了女子?”声音清越,带着悠然的味道,好听是好听,怎么咂摸出幸灾乐祸的意味。小侯爷一天什么也没干,净抖成筛子了。抬头正看到美人黑白分明的眼球幽幽地望着自己。那片温柔的唇正吐着话,一字一个坑,“在下建立琅然宗已经数年,可从未听闻琅然阁的阁主,是个女子。”可不正是青涩的少年味道。姜顺儿这才想起来卷宗里是这么讲的,“胶台有一子,常怀菩萨心肠,行善恩泽东角七年,止兵戈,济难民,时人称曰琅然阁主,日夜奉之。”后面还有一小注,只是连他也不以为然,“形貌娟丽,一颦一笑,惊为天人。”当时他可是嗤之以鼻,笑话,这大桓还有几个容貌能比肩乌平二少的?不过是乡野官吏见识短浅罢了……而赵枫岚脑子里只一片空白:刚幻想出来的儿子没有了,女儿也没有了……娘,平安否,枫岚不大好,列祖列宗那的保佑折子可以撤了……思慕美人三千里,美人有个小兄弟。这般想着,赵枫岚目光有点幽怨,直勾勾移向了趴在琅然臂间,正被爱抚得舒适的老母鸡。那老母鸡长得圆圆滚滚,肉连着毛都快从琅然怀里流出来,承着琅然一下下的抚摸,舒服得把眼都合上了。似乎是感到有不善的目光,竟是摇头晃脑,转了过去,只留一个肥肥的屁股撅着。美人有——叽————!!!娘——————!枫岚想回家!!!…………这件事就像个插曲,一晃而过。琅然早就叫宗内弟子把这次的贡品准备妥当,交个礼单,寒暄几句也就完事了。只可惜那税官仿佛受到了天大打击,之后一直闷闷不乐,情绪低迷。过了没一阵子,琅然就作陪把两人送了出去。回到宅院才刚过正午,看小侯爷那样子也不想留在琅然阁用膳。刚刚的门童和弟子早就都退下不见。平时这琅然阁是不放人的,只是为了应付官员,今天才从外头抽了两个弟子前来帮忙。没了人的琅然阁,安静地有些寂寞……才怪。“然儿!热水已经放好了哦!”一个身影从后院探出来,一身利落的打扮比姜顺儿还专业,一手正探着大木桶里的水温,“温度刚刚好,趁着热乎劲赶快进来。”丰神俊逸的英容早叫炭火给毁了个大半,一手毛巾一手水瓢,小二势头十足。琅然不惊不诧,又顺手薅了两下母鸡,把它放到一边,这才淡定地脱了衣服光溜溜地滑进桶里。瞧也没瞧韩章漠一眼,转身对着小架子上的花镜卸起妆来。韩章漠顶着一脸谄媚到让他吸凉气的笑容,很赶眼色地给他擦背。琅然阁不用侍童,倒也多亏有着这么个全职“小二”。有时候琅然自己也会犯糊涂,好奇他和韩章漠到底谁才是主子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韩章漠算是他爹,可别说亲儿子了,亲媳妇也没这么供养的。那架势倒和韩章漠口头爱挂的那句差不多,“你就是我祖宗。”……“我说,你当年给我做脸的时候,到底用的什么纸。”琅然只觉得自己黑着一张脸,直接让头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转向后方。“黄裱纸,”后者神色如常,放下毛巾企图把他的头别回去。“放屁!你自个瞅瞅,这脸一去妆白的跟个死人一样,你的黄裱纸是硫磺熏的么?”确实,刚刚还顾盼神飞的美人,现在只挂了一张惨白的病容,美则美矣,失了些活灵活现的生气。依稀有青黑的血管攀过额角,两条细缝从眼角滑出复又不见。琅然对着这个滚刀肉气不过,然,尚有一杀手锏未使。桶中玉人默默转身,揪起一根不起眼的眼睫毛。韩章漠眼皮一跳,手快一步摁住了琅然胳膊。桶中顿显分庭抗礼之势,一时僵持不下。“琅然,然儿……然儿啊,你好歹是我找了三年材料,花了七个月才完工的纸傀。全身上下都是天材地宝,不要这么糟蹋自己……这睫毛可是天山雪草的花丝,揪一根少一根……”琅然在心里翻了个惊天大白眼,明明上回还讲是清风崖下玉水虾的虾须。这七年里,大大小小多多少少,不知道被骗了多少次。他只知道自己是个纸傀,还是个能洗澡能吃能撒欢的纸傀。韩章漠总说他涉世未深,不懂事理不明春秋。可他觉得自己该是知道的。就比如他见过自己身上万千傀丝尽数催发的景象,他知道那大概也是一种,森罗地狱。可他亦知道,这个造了自己的人,从未控制过他。想着想着,琅然也就收了力。不巧,某人并没有跟好拍的觉悟。半息间,二人一桶就愉快地一起做伴欢腾到地上。能拿来给纸傀泡的必然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洗澡水,只是眼下琅然顾不得心疼自己滋滋冒响的地砖。果断起身,飞起一脚踹到了韩章漠的屁股上。“你大爷的韩章漠!老子眼珠被你掀没一个!”脸上挂着一个窟窿着实可怕得紧。……青天白日,朗朗乾坤,挺大一个院,就琅然一个傀躺在木桶边沿儿上,数着天上的云发呆。至于韩章漠韩大主子,在给他重新安好眼珠后就被干脆利落地请了出去。倒是没忘让韩小二揣走搁边上闭目养神的老母鸡——那是琅然精心挑了许久的晚饭。他试探地抬起一只手,捏捏脸。虽说硬邦邦的,终究还是赛不过石头。向着那白日铺开手掌,苍白的手虚弱地略显透明,指尖处依稀透出红色。做了个挽花的起手,一道道掌纹,细细的肌理,都在牵拉着活动,清晰可见。哪来的这么好的纸,会有如此细腻的纹路?那掌纹蜿蜒曲折,像鬼魅的蛇信泠然作响,曲向回忆尽头,通向他第一次睁眼,看到这个世界的日子。韩大主子不是没回答过这些个问题。他说纸傀一开始也就是个纸人的样子。几根木杆糊一层纸皮,去哪都是一个样,拿支朱笔点点染染罢了。一切都不过是施术者巧借法阵遮盖的假象。他还是在骗他,这种甜蜜的骗局好像从七年前就早早开始,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明明记着,被韩章漠赋魂,万千傀丝牵引的那天。自己第一眼看见的,就是脚上道道狰狞的疤痕,含着烟灰和血渣。抬起腿搭在桶沿,仔细端详,细想过去,和现在这双脚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也许只是引魂时描的丹砂,不小心糊涂看岔了眼。琅然低头向下看,就算是阵法,是不是也过于真实了点……每每这么想,胯下就有阵阴风吹过,毛毛的。心情在一瞬间变得微妙。暴躁像是燃了引线,飞速从心头烧来,大有燎原之态。琅然暗呼不妙,赶忙从桶中爬起,把一条条经幡铜铃系回发尖,脚掌触地。被刚才那一出闹得,他一下子泡过了点。东角人都晓那琅然宗主坐享天神之姿,发间环佩叮当,经幡翻飞,银铃作响,一双赤足微点,步履悠然,一派仙堂气色,曾引众人争相模仿,一时成为潮流。殊不知,赤足只是为了吸取地气养骨,铜铃与经幡却是为了固魂。毕竟不是人,没有众生的三魂七魄。那所谓的魂魄,不过是韩章漠的一滴血,一口气,远不如寻常人稳定。他每天白日里就在胶台东转转西瞅瞅,玩够回来泡个药浴享享自家主子给的清福,好一个潇洒快活。这些年,韩章漠一次也没控制过他,也从未叫他动用琅然宗去干什么事,就好像历时三年七个月,花那么大精力做这么个傀儡,就是为了供着败家烧钱。他连他主子是什么身份干什么也不知道,家居何方,亲人几何……他只记得七年前的混沌中,是这个人的声音给他指引,让他来到这个世上。是这个人告诉他,他叫琅然,是他的纸傀,除此无他。主子很忙,天天不见身影,还是会回来给他兢兢业业冲药汤,有时他人不在,回来也总是有个小阵法在桶下护着。也许,真的是太寂寞了,所以造个傀儡来陪陪自己解解闷吧。闯个祸,骂个街,偶尔打上一架,和另两个势力斗斗嘴,拆拆楼,挖挖墙角偷偷鱼。怎样都无所谓。仿佛只要他在这里活蹦乱跳的,就已经完成了一切应做的任务。琅然有时也会暗戳戳地想,韩大主子有没有给自己偷偷做颗心。一想到在某个阴沉的下午或阴恻恻的晚上,韩大主子叼着根朱砂笔在他那木架子的胸腔处划来划去,他心情就变得奇好无比。韩大主子其实有点可爱,晚上心满意足喝着喷香鸡汤时,琅然这样想。……而不远处的县令府里,赵枫岚却是躺在床上夜不能寐。翻来覆去把老县令的小破床压得震天响。想起白天美人的盈盈一笑,小侯爷又娇气地嘤出了声。娘,外面的世界套路好深……
小说《一宗之主,就近入土》试读结束,继续阅读请看下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