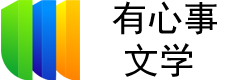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了,深秋的榕城温度还是低的,风吹的我觉得骨头都是凉的。
「舒**,您的身体需要尽快入院治疗。」
医生的话在我脑子里回荡。
我裹紧了身上的外套,在医院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也没等到季池。
他估计早就忘记了自己说的要来接我的话了。
我也懒得给他打电话质问了,没意思的事,就算我打过去抱怨,季池也不会理会,他根本不在乎我,自然不在乎我说什么。
「年年,怎么一个人在这里?」
除了我家人很少有人这么叫我的名字,我有些意外地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,竟然是宋应。
我和宋应很久没见了,上一次见应该还是高中的时候了。
后来我因为父母离异我跟着妈妈离开了老家,我们俩也就因此断了联系。
宋应现如今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吊儿郎当的少年了。
他现在穿着白大褂,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,看起来就是值得信赖的医生模样。
还真是男大十八变。
「你怎么也来榕城了?」
宋应指了指身后的医院,笑着回答我的问题,「我在这工作。」
「你呢?你是身体不舒服吗?看着脸色不太好。」
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我自然没告诉宋应我生病的事。
随便找了借口,「我来这边看朋友。」
没和宋应聊两句,家里的司机陈叔就开着车来接我了。
车停在我和宋应对面,车窗缓缓落下,紧接着传来陈叔关心的声音。
「太太,该回去了。」
我看了眼车就知道不是陈叔一个人来的,季池也一定在车上。
陈叔自己来接我的时候从来不会开这种千万级别的车的,只有接送季池的时候才会开这种车。
季池这个人很傲,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向来没什么耐心。
而我又恰恰是他最讨厌的人,来接我也是他讨厌的事。
叠满了,不用想我就知道他此刻表情得多臭。
我无心应付他的毒舌,也就不敢让他多等,和宋应匆匆告别,我就快步走到了车旁边。
陈叔看我过来了,也下车替我开了车门。
我上车的时候用余光撇到了坐在里面的季池,他似乎也看我了我一眼,眼神不太友好,一脸很不耐烦的样子。
我知道他不高兴了。
懒得和他吵架,我也没主动说话触他的霉头。
就只是安静地坐那里,身子紧紧地贴着挨着门的一侧,离季池保持一定的距离,我想让他忽略我的存在。
但季池显然不想如我的愿,他握着我的手臂,冷着声「舒年,你就那么怕我?」
我以为他又要说难听的话羞辱我了,到没想到他说了这么一句,我被他的话搞得说的一愣,侧过头有些不解地看他。
内心偷偷腹诽他这又是吃错什么药了?
估计是见我没有回应,季池又冷了脸,声音放的很低像是在警告我一般。
「怕就滚下去,别搞这副样子在这里碍眼。」
可能是要死了的缘故,也可能是被季池这冰冷的语气给**的,我突然就觉得委屈地要命。
他季池凭什么这么对我啊,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
这个王八蛋!
情绪来的很快,我委屈地要命,眼泪也是说来就来,在眼眶里打转,但我不想在季池面前哭,就好像在示弱一般。
我倔强地不眨眼,红着眼眶直视着季池,片刻转过头对着前面喊道。
「陈叔停车,我要下去。」
陈叔不愧是季池家的老司机,别看平时对我言听计从的,真到这种时候他是向着季池的,我说什么他根本不听。
趁着红灯的功夫他看了眼季池,然后才开口说「太太,先生他没有恶意的。」
言下之意就是不可能听我的。
其实退一万步讲我也理解他,毕竟职场上谁给钱谁就是老大,是季池给他发工资,他肯定得听季池的。
但我还是觉得委屈,也不知道在委屈什么,我扭过头不想理会季池,看向窗外,眼睛有些酸涩,我眨了眨眼睛,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了。
季池要替我擦眼泪,被我躲开了,他的手僵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收回去。
「停车陈叔,让她下去。」
我是走回别墅的,从下午到晚上一共走了四个小时。
期间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,季池也没有。
好不容易走到家我腿软的要命,胃也和针扎的一样特别疼。
我瘫在沙发上缓了好一会儿才坐起来,想找点药吃,这才想起来在医院拿的药以及我的包全都忘在季池的车上了。
胃疼的我没有胃口,也根本吃不下饭,最后我只是喝了点温水就上楼了,一直在床上睡了两个多小时才醒来。
醒来我头晕的厉害,又睡不着了,我去楼下热了杯牛奶在客厅待了一会儿,家里的管家刘姨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吃晚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