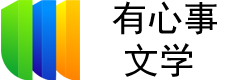第二日清晨,下起了蒙蒙细雨,沥沥淅淅的打在发青的屋檐上,溅起片片白茫茫的水花。
群众们打着油纸伞,早早就聚集在衙门口,默默等待着他们的沈大夫平安归来。
大堂上,翁岭详细的询问了证人证词,老板娘与鹤堂主依然一口咬定朱老板是喝了沈琴的药而亡。
何县令奴颜婢膝的站在翁岭旁边,委屈巴巴地辩解道,
“大人,您看,下官没有判错,就是沈琴害了人命。”
翁岭没有搭理他,直接问沈琴道,
“你有什么为自己辩解的吗?”
跪在堂下的沈琴深吸一口气,俯身将自己的意思写在纸上,由浩儿读出来。
[草民有些疑问,望大人允许草民问下证人。]
翁岭点头默许。
沈琴看向老板娘,写道,
[夫人,试问天下有几个妻子见丈夫倒下了,非但不急,还出言让大夫慢慢治的?]
老板娘脸色微变,有些磕巴的说道,“这、这有什么奇怪的,妾身只是怕鹤堂主一时心急给治错了。”
[所以他真治错了。]
沈琴用犀利的目光扫了鹤堂主一眼,
[鹤堂主作为曾经的太医,为何连简单的胸痹都看不出,按照中风来治,针法皆为散气,是盼着朱老板快点归西吗?]
鹤堂主逃避了沈琴的目光,脸一红,“算本人医术不精吧。”
换了张纸,沈琴又写道,
[那后来,鹤堂主指出附子剂量过大,会导致中毒之时,夫人为何在沈某喂药之后才出言威胁,正常不应该在服药之前就阻止吗?]
老板娘嗫嚅道,“我、我就是天生反应慢。”
沈琴冷笑了下,快速在纸上写道,
[还是说,你们一开始就希望朱老板早点死,而沈某的出现刚好做了替罪羊?]
老板娘瞪大了凤目,指着沈琴尖叫道。
“你血口喷人!妾身为什么要盼着自己丈夫死?”
鹤堂主抱着胳膊,不满的撇撇嘴,
“怎么能凭几句话就把脏水泼到本堂主身上,朱老板是次日早上服药而亡的,药材也是从你那里拿的,与本堂主有何关系?”
老板娘眼泪哗哗的就流了出来,跪着给翁岭磕头,
“是啊,大人要为妾身做主啊,妾身命苦,早早就成了寡妇,还要被这个姓沈的庸医如此诬陷!妾身都不想活了……呜呜呜。”
“肃静!“翁岭猛拍惊堂木,厉声道,“这里是公堂,不是你哭丧的地方!”
老板娘立刻把哭声憋了回去。
翁岭对沈琴严肃的说道,
“沈琴,这些只能作为疑点,不能作为证据,你还有别的辩词么?”
沈琴写道,[草民可否看看药渣。]
翁岭一招手,仵作把证物呈了上来,药渣均已晾干,里面的品种也都分了出来,摊开在粗黄纸上。
“都已核对过了,与沈大夫所开药方,剂量类似,种类也是一样的。”
沈琴仔细审视了下附片,拿出其中两片放在口中轻舔了下,心中有了答案,
[大人,这附子让人调换过了。]
翁岭问道,“何以见得?”
沈琴写道,[草民所开的是炮附子,仅三钱,且有甘草、生姜辅佐,煮后不应麻舌,就算是煎煮时间短,以朱老板的体型来说,也不足以致命,而此附子中掺有灰白片,尝之麻舌,草民认为当是生草乌。]
翁岭好奇道,“这生草乌又是何药?”
[草乌与川乌同种类,而附子是川乌的子根,三者极为类似,但论毒性,炮附子最低,生川乌其次,而生草乌最毒,所以草民认为真正导致朱老板中毒的就是生草乌。]
翁岭立刻会意,“你是说,有人故意将部分炮附子换成生草乌,毒杀朱老板?”
此言一出,全场震惊。
老板娘、鹤堂主皆面露紧张。
沈琴提议,当场做实验,翁岭便叫人拿来几只老鼠,将药渣中的草乌片、炮附子片捣碎掺入食物中,分别喂给老鼠吃,服用草乌片的老鼠很快殒命。
见案件有了转机,翁岭一挥袖子,“来人,宣本案所有证人到堂对质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