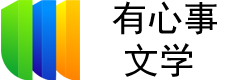嫂子,对不起,都怪我笨手笨脚……白玲玲靠在他怀里,哭得梨花带雨。
他失望地看着我:你就不能大度点?我笑了。大度?我的大度很贵,从不施舍给垃圾。
而你,江潮,马上就会知道。我真正的大度,给了谁。1红旗下的决裂红旗招展,
锣鼓喧天。今天是红星机械厂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。我的丈夫江潮,
作为最年轻的科长、全厂最耀眼的先进标兵。正站在主席台上,意气风发地念着发言稿。
……我们工人,要一手抓生产,一手抓思想,两手都要硬!台下掌声雷动。
我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袋,里面是刚出锅的肉包子和一盒搪瓷饭盒装的的小米粥,
挤在人群的最后面。江潮有老胃病,我知道,他早上为了准备发言,肯定又没吃饭。
他的发言结束,是全场最**。厂长亲自给他戴上大红花,掌声经久不息。我算准了时间,
在他走下台,被一群同事和领导簇拥着的时候,迎了上去。江潮,我把帆布袋递过去,
趁热吃点东西垫垫。他脸上的笑容,在看到我和我手里的帆布袋时,瞬间凝固了。
那是一种训练有素的、可以瞬间切换的表情。前一秒还是春风得意,
下一秒就成了冰封的湖面。他没有接。周围的恭维声和笑声,似乎也因为他表情的变化,
而短暂地停滞了一下。他把我拽到后台的幕布后面,那里堆满了废弃的道具,
散发着一股霉味。林晚,你来干什么?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但充满了怒火。
我来给你送饭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袋子,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。
谁让你来的?你看看你穿的什么?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饭盒,没有打开。
而是重重地放在旁边的破旧木箱上,发出哐当一声巨响。你就不能注意点影响?
他逼近一步,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。一字一句地,
从牙缝里挤出那句上辈子我听到过无数次的话:我的脸,迟早让你丢尽。我看着他。
看着他穿着我连夜熨烫的白衬衫,胸前戴着象征荣誉的大红花,脸因为愤怒而微微扭曲。
上辈子,我听到这句话时,只觉得无地自容。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,是我给他丢了人,
是我这个糟糠之妻,成了他进步路上的污点。我为此自卑、惶恐,拼命想追上他的脚步,
却被他越甩越远。直到最后,他为了娶厂长的女儿,设计我出轨,让我净身出户,
在流言蜚语中病死在那个湿冷的雨夜。而现在。重生回来的我,再次听到这句话,
心脏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,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。江潮,我开口,
声音冷静得让自己都有些意外,我们离婚吧。2离婚风暴江潮愣住了。
他大概以为我会像从前一样,要么唯唯诺诺地道歉,要么红着眼睛与他争辩。
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三个字。你说什么?他掏了掏耳朵,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我说,
我们离婚。我重复了一遍,语气没有丝毫起伏,然后转身就想走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,
力气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。林晚,你又在耍什么把戏?就因为我说了你两句?
他的眉头紧锁,那种熟悉的、高高在上的不耐烦又回到了脸上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?
我今天是什么场合?厂领导都在,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?他永远都是这样。错的永远是我。
他关心的永远是他的面子,他的前途,他的人设。我平静地挣开他的手:我没有耍把戏,
江潮。我是认真的。认真?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嗤笑一声。你离开我,
你能活吗?你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村女人,除了洗衣做饭,你还会干什么?离婚?
谁给你的底气?这番话,和上辈子他在逼我离婚时说的,一模一样。那时,
我被这些话刺得体无完肤,觉得天都塌了。现在,我只觉得可笑。这是我的事,
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理了理被他抓皱的衣袖,离婚协议,我会尽快写好。说完,
我不再看他那张由震惊、愤怒、鄙夷交织成的复杂面孔,径直走出了幕布。
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,表彰大会已经结束。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,脸上还洋溢着兴奋。
没人知道,在刚刚那个阴暗的角落里,他们眼中的天作之合,已经分崩离析。
回到那个被称之为家的小屋,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。
这个家里,处处都是江潮的痕迹。书架上摆满了他爱看的《参考消息》和各类文学名著。
墙上贴着他先进标兵的奖状,就连床头,都放着他学习俄语的词典。属于我的东西,
只有几件旧衣服,和我母亲留给我的一个木匣子。打开木匣子,
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——三百二十六块钱,还有几张粮票、布票。这是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。
上辈子,这笔钱在我被赶出家门后,成了江潮和白玲玲新婚旅行的费用。这一世,
它将是我的启动资金。晚上,江潮回来了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质问我为什么没做饭。
而是在桌子对面坐下,点了一根烟。青色的烟雾缭绕,模糊了他英俊却凉薄的脸。林晚,
我今天话说得是重了点。他先开了口,摆出了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。
但你也要理解我。我现在的位置,多少人盯着?行差踏错一步,就是万丈深渊。
我需要的是一个能为我增光添彩的妻子,而不是一个给我拖后腿的。他顿了顿,
弹了弹烟灰,继续用他那套理论说教。你今天提离婚,我知道是气话。我不跟你计较。
以后,少往厂里跑,有什么事,等我回家再说。还有,多看看书,学学文化,
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柴米油盐。我静静地听他说完,
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我已经写好的离婚协议,推到他面前。江潮,我不是在说气话。
他脸上的从容和伪装的耐心,终于寸寸碎裂。3白莲花的阴谋林晚,你别不知好歹!
江潮猛地站起来,一巴掌拍在桌子上,那份薄薄的离婚协议被震得跳了一下。
你以为我不敢离是吗?我告诉你,想嫁给我的女人,能从厂门口排到大街上!
其中不乏大学生、干部子女!你算个什么东西?他气急败坏的样子,
让我心里最后一点残存的旧日情分,也烟消云散了。我点点头:我知道。
所以我是在成全你。我的平静,像一拳打在棉花上,让他所有的怒火都无处发泄,
只能憋在胸口,脸色涨成了猪肝色。正在这时,门口传来笃笃的敲门声。江科长,
在家吗?一个柔媚得能掐出水的声音响起。是白玲玲。厂里新来的技术员,
刚从技术学校毕业,一双大眼睛总是水汪汪的,看谁都像是在求助。上辈子,
她就是踩着我的尸骨,成了江潮的第二任妻子。江潮的脸色变了变,迅速收敛起怒容,
过去开了门。是小白啊,有事吗?他的声音,瞬间变得温和可亲。江科长,
白玲玲怯生生地站在门口,手里捧着一个搪瓷杯。我……我听王姐说你胃不好,
晚上也没吃饭,就……就给你冲了杯麦乳精。她的目光越过江潮,落在我身上,
立刻像是受惊的小鹿,瑟缩了一下,声音更低了:啊……嫂子也在啊。对不起对不起,
我不知道……我这就走。她说着要走,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,一动不动,
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里,迅速蓄满了委屈的泪水。好一朵盛世白莲。江潮立刻回头,
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,仿佛我是一个会吃人的恶婆娘。你这是干什么?小白也是一片好心。
他侧过身,让白玲玲进来,进来坐,别理她,她今天心情不好。不不不,江科长,
都是我的错,我不该这么晚来打扰你们。白玲玲把麦乳精塞到江潮手里,
眼泪终于掉了下来,嫂子你别误会,我和江科长真的没什么,
我只是很崇拜他……她这番表演,句句都在撇清,却又句句都在暗示。上辈子,
我就是这样被她一步步逼到墙角,被所有人误会成一个蛮不讲理的妒妇。这一次,
我连眼皮都懒得抬。我只是把那份离婚协议又往前推了推,看着江潮,
冷冷地吐出两个字:签字。江潮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。当着他需要保护的白月光,
我的不识大体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。好!林晚,这可是你自找的!他抓起笔,
刷刷两下,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你给我滚!现在就滚!白玲玲在一旁,
嘴角勾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,随即又换上担忧的表情,拉着江潮的胳膊:江科长,
你别生气,嫂子她……她以后不是你嫂子了!江潮一把甩开她的手,
指着门口对我吼道。我一言不发,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,拎起我早就收拾好的小包袱。
在他们两人错愕的目光中,干脆利落地走了出去。带上门的那一刻,
我听到了白玲玲的惊呼和江潮压抑的喘息。我知道,从今天起,我自由了。我的复仇,
也正式开始了。4复仇的种子我和江潮离婚的消息,像一阵风,
迅速传遍了整个红星机械厂。版本有很多。流传最广的,是陈世美和妒妇的版本。
说我林晚是个没文化、爱猜忌的农村女人,配不上前途无量的江科长。江科长念旧情,
不忍抛弃糟糠妻,我却天天在家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甚至冤枉他和冰清玉洁的白技术员有染,
江科长忍无可忍,才终于同意离婚。在这个故事里,江潮是仁至义尽的受害者,
白玲玲是无辜被牵连的白莲花。而我,是那个阻碍进步、思想落后的绊脚石。我能想象,
这些流言背后,白玲玲和江潮功不可没。江潮需要维持他仁义的面子,
白玲玲则需要为自己上位扫清舆论障碍。我没有去辩解。因为我知道,对付他们,
口水是最无用的武器。我用离婚分到的(或者说,是我拿回来的)三百多块钱,
在城西一个偏僻的筒子楼里租了个小单间。然后,我开始执行我的计划。第一步,
是找到王进。王进是厂里一个不起眼的技术员,三十出头,戴着厚厚的眼镜,性格木讷,
不善言辞。但他是个技术狂人。上辈子,就是他,在几年后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切割机床。
效率比厂里现有的苏联老机器高出五倍,一举成名,后来更是自己办厂,
成了机械行业的巨头。而江潮,是他一辈子的死对头。因为现在,
王进正因为一个技术革新的提案,被江潮死死地压着。
江潮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、好高骛远,会打乱生产秩序,影响自己的政绩。
我找到王进的时候,他正在一个昏暗的小酒馆里,就着一盘花生米喝着闷酒。他的面前,
散落着几张被揉得皱巴巴的图纸。我走过去,在他对面坐下。王工。他抬起头,
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迷茫,显然不认识我。你是?我是林晚,江潮的前妻。
我开门见山。他愣了一下,眼神里闪过一丝戒备和尴尬。我没理会他的神情,
直接从包里拿出我所有的钱,推到他面前。我想投资你。王进彻底懵了,
他看着桌上的那堆钱,又看看我,结结巴巴地说: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?意思就是,
我看着他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。我相信你的技术,远比江潮的‘面子’,值钱得多。
5命运的转折王进的第一反应是拒绝。他以为我是江潮派来羞辱他的,
或是另有什么阴谋。我不需要你的可怜。他涨红了脸,把钱推了回来。这不是可怜,
是交易。我没有动,只是平静地看着他。我知道,
你的提案需要一种特殊的合金材料做实验,厂里不批,你自己买不起。我顿了顿,
抛出了我的第一个筹码:我知道一个地方,能用最低的价格,买到这种材料。上辈子,
江潮为了打压王进,曾得意洋洋地在我面前炫耀过。他如何利用职权,
卡住了王进所有能搞到实验材料的渠道。而江潮在向我炫耀他如何堵死王进所有渠道时。
我从他无意中透露的只言片语里,
拼凑出了一个被他忽略掉的信息:一个即将处理废料的军工厂仓库里,
恰好就有王进需要的那种高强度合金。他认为那是没用的废铁,我却记在了心里。
王进的眼神变了。从戒备,变成了震惊和怀疑。你怎么知道?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,
我说,你只需要回答我,干,还是不干。他死死地盯着我,厚厚的镜片后面,
目光闪烁。半晌,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,猛地灌下一口酒。好!**!但是,
我不能白拿你的钱。等我的项目成功了,我双倍,不,十倍还给你!我不要你还钱。
我摇了摇头,说出了我的最终目的。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?
将来,无论你达到什么样的高度,只要江潮还在红星机械厂一天,你就留在红星机械厂,
当他一辈子的‘对-头’。我要的,不是钱。我要的,是诛心。
是让江潮这个把面子看得比天大的人,亲眼看着被他踩在脚下的垃圾。
一步步爬到他的头顶,成为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。王进怔怔地看着我,许久,
他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我答应你。我们的同盟,就在这个破旧的小酒馆里,正式结成了。
接下来的日子,我用上辈子的记忆,带着王进。去那个即将废弃的仓库,
用几乎是废铁的价格,买到了那批珍贵的合金材料。又用剩下的钱,
租了一个废弃的车库当做临时实验室。王进像是个疯子一样,一头扎了进去,
没日没夜地做着实验。而我,则在外面,为他处理一切后顾之忧。与此同时,
江潮和白玲玲的日子,过得风生水起。他们很快就订了婚,在厂里出双入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