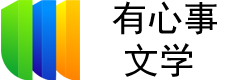流放路上,柳如烟用我送她的银簪捅穿喉咙。蘸着喉头血,
站墙上写下一个歪扭的‘悔’——就像当年她在我认罪书上按的手印1毒蛛缠心砚哥哥,
认罪吧。不过是一坛御酒,认了,流放三年而已…我等你。柳如烟的声音像淬了毒的蛛丝,
缠绕在我被剧痛撕扯的神经上。
她绯红的宫装裙裾拂过我蜷缩在地、沾满血污和碎颜料的指尖,金线绣成的牡丹冰冷刺眼。
我没抬头,视线被额角淌下的血模糊,
喉咙里全是铁锈味:我没碰那酒…更没酒后失仪…毁坏贡品…阴影里传来一声嗤笑。
陈子昂踱步而出,腰间翰林院的金鱼袋晃得人眼晕。他蹲下身,
玉扳指故意碾过我碎裂的腕骨,钻心的痛让我眼前一黑。萧兄啊,人赃俱获,抵赖何用?
他虚伪的叹息里是藏不住的得意,从你画案底下翻出的空酒坛,可是众目睽睽!昨日,
就是这只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手,执着画笔,在柳如烟含情脉脉的注视下,
勾勒出《千里江山图》磅礴的初稿。脏手…拿开!我牙关紧咬。陈子昂眼底戾气一闪,
皂靴猛地抬起,狠狠踩下!咔嚓!又一声脆响!比廷杖更尖锐的痛楚炸开!意识模糊前,
我瞥见柳如烟飞快别过脸,可她腰间那枚崭新的羊脂白玉佩,上面那个小小的陈字,
像烧红的烙铁烫进我眼底。那是我熬了三个月夜,替人画了无数低廉扇面屏风,
才为她换来的生辰礼。心,比手更冷,更空。2雨夜绝情罪人萧砚,酒后失仪,
污毁贡品!杖八十!永不许执笔!逐出宫门!太监尖利的宣判割裂空气。
沉重的廷杖裹着风声砸下,皮开肉绽。我死死盯着丹陛,陈子昂正虔诚接过御赐的紫毫笔,
嘴角压不住地上扬。柳如烟立在他身后,绞着素白丝帕,指节泛白。八十杖打完,
我被像破布般拖过漫长宫道,身后蜿蜒着刺目的血痕。宫门外,暴雨如注。
血水混着雨水在青石板上流淌。我被扔在宫墙根幽暗的窄巷里,冰冷的雨水冲刷着伤口。
更夫的梆子空洞地敲过三下。踉跄的脚步声停在面前。半旧的油纸伞移开,
露出柳如烟脂粉斑驳的脸。
乱地将一个湿漉漉的包袱丢进泥水:银票…金疮药…去南边…永远别再回京…包袱散开,
几张被雨水泡烂的薄银票粘在泥里。呵…我嗤笑出声,混着血沫,
陈夫人…打发叫花子?她浑身剧颤:砚哥哥!子昂他说…我不来…就要你命!
他做得出的…滚!巷口骤然响起马蹄声,火把的光撕裂雨夜。陈府家丁围拢。夫人!
少爷请您回府试凤冠霞帔!柳如烟最后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复杂,最终化为决绝。
她猛地转身,奔向巷口那片暖黄的光晕。嫁衣上的金线牡丹在火光下流光溢彩,
像扑火的飞蛾。你看清楚!她尖利的声音在雨中回荡,你这手废了!彻彻底底废了!
除了我…这世上还有谁要你这样一个废人?!雨,更冷了,仿佛要冻结骨髓。
3沙地重生塞外的风,裹着沙砾,刀子般刮在脸上。边军粮草营,
弥漫着马料、汗臭和尘土的气息。我佝偻着腰,用僵硬笨拙的左手,
在油腻的羊皮账簿上记录数字。墨迹歪斜如蚯蚓。废物!满脸横肉的伍长抓起羊皮纸,
狠狠啐在我脸上,写的什么狗爬!连胡儿崽子都不如!营妓们的哄笑刺耳。
一个穿破红裙的女人踢了踢角落的劣质颜料罐:喂,画师?手废了,眼没瞎吧?
画个春宫图瞧瞧?赏你口酒喝!哄笑声更大了。左腕旧伤在寒夜里钻心地痛。
我蜷缩在角落,抓起一把细沙,用冻裂渗血的左手食指,在冰冷粗糙的沙地上,
一笔一划地勾画远处的沙丘。风沙呜咽着抹平线条。我不停,再画。血混着沙粒,
画出更深的痕迹。画盘旋的鹰隼,画孤独的烽燧。三个月,日复一日。指尖的血痂结了又破。
左手渐渐驯服。第一幅完整的《大漠孤烟图》画在粗糙羊皮上。
一个路过的胡商指着画中鹰隼,铜铃大眼放光:像!真像!上月叼走我母羊的就是它!
他丢给我三张厚实的胡饼。我攥着饼,目光落在画上。
粮草营昏黄的火光在画角晕开一小片模糊的暖橘,像极了承明殿令人作呕的宫灯。
鹰爪下的沙丘暗影里,我用极细的笔触,藏进一方微小却棱角分明的砚台轮廓。吾名萧砚。
断手,未断魂。4龙帖之谜无名先生的名号,如塞外旋风席卷江南。左手执笔,
画风奇崛。烟雨有了筋骨,风雪淬出锋芒。千金难求一纸。先生,
临安城望江楼老板毕恭毕敬递上烫金名帖,有位顶顶尊贵的贵人,求您赐一幅千秋寿礼。
名帖上,五爪金龙盘绕。落款处,一个笔力遒劲的陈字,刺目如毒钩。皇后千秋。
陈子昂必在。我搁下旧笔,一滴浓墨,恰好滴溅在那刺目的陈字上,
晕开一团化不开的黑。接。5红莲惊变画舫驶入京城运河,两岸人山人海。快看!
无名先生的‘莲舟’!天爷啊!十里红莲!神迹!赤红如血的莲,绵延十里,
覆盖河面。十二幅丈余工笔莲图缀满画舫朱栏,映得运河如流淌岩浆。辉煌壮丽,摄人心魄。
皇后凤辇停在码头。内侍总管尖声长宣:宣——无名先生觐见——我踏上跳板,
青铜獠牙面具覆面,素色布袍在河风中翻飞。画舫内,丝竹靡靡,衣香鬓影。
目光透过面具孔洞扫过。陈子昂端坐翰林院首席,柳如烟依偎在侧,云鬓东珠微颤。她侧首,
葱指慵懒指向栏外红莲,声音娇憨刻薄:子昂你看,这红莲虽多,却艳俗匠气,
怎及你《江川揽胜图》万一?那才是气韵生动,意境高…话音,在我踏上主舱,
缓缓摘下面具的刹那,戛然而止。满场死寂。丝竹停,谈笑歇。当啷!
陈子昂的玉杯脱手坠地,摔得粉碎。他脸色惨白如纸,僵直如遭雷击。萧…萧砚?!
柳如烟猛地站起,带翻玛瑙果盘,惊骇欲绝如同见鬼。皇后凤目微挑:萧画师?
三年前…那个污毁贡酒,被逐出宫门的…正是罪民。我躬身。皇后娘娘明鉴!
陈子昂猛地弹起,冲到中央噗通跪下,声音恐惧扭曲,此人是戴罪之身!污点未清!
岂能近凤驾!他慌乱抖出一卷画轴高举,臣…臣新作《瑶池仙寿图》,
愿献娘娘…陈翰林,皇后指尖轻叩扶手,目光落在他筛糠般颤抖的手上,
你抖得厉害啊。是画舫不稳,还是你…心虚了?压抑的低笑响起,化作一片哄堂大笑。
陈子昂面红耳赤,羞愤欲死。柳如烟慌忙跪下,身体抖如筛糠,怨毒地瞪着我。
皇后目光转向我:萧先生这满河红莲,金红交融,艳而不妖,是何妙法?回娘娘,
我展开《千莲朝凤图》,金粉掺茜草汁,三曝三蒸,取其浓烈纯粹,再以松烟调和,
方得此金中蕴赤,赤中流金。画卷展开,金红莲瓣在日光下流淌熔金般光泽,
莲心似有金粉浮动,磅礴圣洁。满座倒抽冷气。柳如烟死死盯着画,脸上血色褪尽,
失魂落魄。那神韵气魄,是陈子昂偷来的画拍马难及!好!好一个‘金中蕴赤,
赤中流金’!妙极!皇后抚掌,赏萧先生紫金冠!赐座!紫金冠沉沉压上发髻。
陈子昂眼中淬毒,嫉恨欲燃。柳如烟像是被刺中心魂,
凄厉哭喊着拨开人群扑来:砚哥哥——!她跪倒在我脚边,泪水汹涌,
你的手…你的手怎么样了?!她伸手欲抓我左手腕。我衣袖微动,
右手腕骨处狰狞凸起、皮肉扭曲的旧伤疤暴露在光线下。满座哗然!如烟!滚回来!
陈子昂目眦欲裂,冲来拽她。陈子昂尖利的嘶吼:皇后娘娘!此等戴罪贱奴,妖言惑众!
怎配污了您的寿宴!他额头重重磕地,他萧砚!三年前便酗酒渎职,污毁御酒,
品行不端!此乃铁案!如今定是学了塞外胡人邪术蛊惑人心!这满河红莲,妖异浮夸!
绝非正道!陈翰林慎言!老翰林气得胡子直抖。慎言?我说错了吗?
陈子昂摇摇晃晃站起,脸上是破釜沉舟的扭曲,他环视全场,声音陡然拔高,
充满恶毒揣测,诸位想想!塞北苦寒军营,都是些什么货色?他一个断了手的废人,
凭什么活下来?还练就这一手邪门的左手画技?他发出一串令人作呕的嗤笑,
呵…怕不是靠着在那些粗鄙军汉、甚至胡人蛮子的帐中…曲意承欢,当个**的脔宠,
用这伺候人的‘手上功夫’换来的苟活吧?这等腌臜秽物,也敢登大雅之堂!污了娘娘圣目!
脏了这满河红莲!你…你血口喷人!几位官员拍案而起。
柳如烟也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,强撑着站起身,指着画舫外,
指尖因激动和恶毒而发颤:陈翰林所言极是!娘娘!您细看!这红莲铺张诡异,金粉俗艳!
绝非我中原正道画风!定是邪术!一个右手尽废的残废,左手能画出什么?
怕是连笔都拿不稳!娘娘万金之躯,莫要被这秽物污了凤体!够了!
皇后含霜的声音刺穿喧嚣。她凤目扫过状若疯魔的二人,画舫内落针可闻。
就在这时——肃静——!长公主殿下驾到——!清越悠长的通传,如裂帛之音,
骤然划破死寂!所有人猛地转向画舫入口。朱漆舱门被两名银甲女官缓缓推开。
门外辉煌的红莲之光流淌进来,映出一道被众多宫婢簇拥着的高华身影。长公主殿下,
一袭绯红蹙金绣鸾凤宫装,云髻巍峨。她未乘肩舆,亲自抱着一个明黄锦缎襁褓,步履从容,
仪态万方。那通身的气度,瞬间压下满船珠翠。她的目光,如穿透迷雾的利剑,
越过跪地的陈柳二人,越过惊疑的满座宾客,精准地落在我身上。然后,
在所有人惊愕到失语的注视下,长公主抱着婴孩,径直向我走来。裙裾无声拂过地面,
每一步都踏在众人心尖。她停在我面前一步之遥。无视高位上的皇后,无视任何人。
她微微倾身,动作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,将怀中那温软锦缎襁褓,
稳稳地塞进我的臂弯。襁褓温热,带着奶香。小婴儿被惊动,乌溜溜的眼睛睁开,小嘴一瘪,
发出嘹亮哭声:哇啊——!哭声在死寂中如同惊雷!长公主这才抬眼,
那双凤眸清冷如寒潭古玉,扫过全场惊骇欲绝的面孔,落回我脸上,声音不高,
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,带着理所当然的慵懒和一丝嗔怪:驸马,麟儿哭闹半日了,
非要寻你。你这当爹的,只顾着在此作画,连孩儿都忘了么?还不随本宫回府,
给麟儿画幅小像?驸马?!爹?!两道九天玄雷,狠狠劈在众人头顶!轰——!
死寂彻底炸裂!惊呼、抽气、杯盘碰撞声爆开!驸…驸马?!长公主叫他什么?
驸马?!爹?!那个孩子…是…是他的?!萧砚?!他…他是长公主殿下的驸马?!
怎么可能!陈子昂如同被抽走骨头,彻底瘫软在地,眼珠暴突,脸上血色褪尽,
只剩濒死的灰败。喉咙里发出嗬嗬怪响,一个字也吐不出。柳如烟则像被巨锤砸中心脏!
她猛地抬头,脸上所有怨毒、得意、高傲瞬间粉碎!她死死盯着长公主,又转向我怀中婴儿,
最后凝固在我脸上,脸庞扭曲变形,瞳孔因极度的震惊、恐慌和灭顶的绝望疯狂扩散!
不…不可能!她失声尖叫,凄厉如夜枭,假的!一定是假的!他一个断了手的废人!
一个流放塞北的罪奴!怎么可能攀得上长公主!怎么可能…是驸马?!她指着我怀中婴儿,
手指抖如枯叶,这野种…这野种是谁的?!萧砚!你说!是不是你找来的戏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