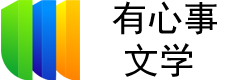老公的道士青梅华黎归来,看见我的汤臣一品别墅便双眼冒光。这房子,
是我命里该有的房子。你占了我的房子,是要遭报应的,这里已经变成凶宅了!
老公纪南星也跟着劝我,老婆,凶宅可不能住啊,你听话,把别墅还给她吧。还给她?
她几句玄语就把我的房子归为她的,真不要脸。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。
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。没过多久,我就在别墅里撞见了老公与他的青梅在共度良宵。
房间里,华黎搂着纪南星的脖子笑得甜蜜,你说把这个房子送我了,你得信守承诺啊。
纪南星信誓旦旦地说:那肯定,我老婆这个人最胆小了,
我们只需要小小地装神弄鬼一下,这房子就是你的了。我转身回了房间,
拨通了我那手握京城命脉的母亲的电话。妈,你送你女儿我的新婚礼物被人惦记上了,
你管不管?1挂断电话,我静静地坐在床沿。纪南星推门进来的时候,手里端着一杯牛奶,
脸上挂着温和的笑。还在为华黎的事生气?她也是为我们好。他走过来,
将牛奶递到我面前。别多想了,喝完牛奶早点睡。我接了过来,随手放在床头柜上,
我不想喝。纪南星的笑容僵了一下,但很快又恢复如常。
你不是每天晚上必喝一杯热牛奶吗?不要为了别人生气,而亏待自己。他拿起杯子,
重新送到我嘴边。乖,听话,我看着你喝完。我不想在这种小事上与他拉扯,仰起头,
将那杯牛奶一饮而尽。他满意地笑了,拿走空杯子,在我额上印下一个晚安吻。睡吧。
夜半时分,我突然被腹部一阵剧烈的绞痛痛醒。我挣扎打完120就晕了过去。
检查结果出来,医生说,是吃坏了东西。我躺在洁白的病床上,看着天花板,心中一片冰冷。
第二天,我回到别墅。华黎正在客厅跳大神。她看着我苍白的脸色,手指在空中比比划划,
你看,我说了吧!这宅子里的脏东西已经对你下手了!你没有功德护体,
在这里待久了,轻则生病,重则丧命!她一脸严肃,仿佛神明附体。今天,
我就要在这里开坛做法,为你驱邪!纪南星立刻附和。是啊,老婆,华黎是大师,
她不会看错的。之前有好多人都来找她做法呢,排都排不上号,你也是沾了我的光了。
他握住我的手,满眼关切。这房子真的不能住了,我们那么多房子,这套就还给华黎吧。
我看着他,忽然觉得无比陌生。我想起了昨晚那杯牛奶。我放杯子的时候手抖了一下,
洒了一些在了床头柜上。我没有声张,让保姆将我房间里的一块桌垫送去检验。
检验结果回来得很快。他们在上面检测出了高浓度的泄药成分。我拿到结果的时候,
他们还在装模做样地为我祈福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冷冷地开口。这栋别墅,
你们别想了。除非我死,否则这栋别墅,你们一根柱子都别想拿到。
纪南星的脸色变了。你说什么胡话,这是为你好!华黎也皱起眉。
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?当天晚上,我听见华黎在房间里对纪南星发脾气。
你不是说她很好骗吗?现在怎么办?你答应过我的,这栋别墅是我的!
纪南星在低声安抚。你别急,再让我想想办法,一定有办法的。我没有再听下去。
我回到房间,关上门,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你好,王律师。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。
2和律师谈完所有细节,已经是下午。回到家,我却找不到我的大黑狗旺财了。
我立刻发动了别墅里所有的保姆和园丁,里里外外地找。最后,
旺财被发现死在了没有监控的阁楼,身上有被钝器反复殴打的痕迹。我冲过去,
抱住它冰冷的身体,眼泪再也控制不住。旺财是我从它刚出生就抱回来的,它陪了我很多年,
已然是亲人一样的存在。纪南星跟着跑上来,看到旺财的尸体,夸张地叫了一声。天哪!
怎么会这样!他一脸惊慌,拉着我的胳膊。老婆,你看,这别墅真的太凶了!
连狗都……我们快搬走吧!这里不能住了!我甩开他的手,声音嘶哑,
我一定要查出来,是谁杀了旺财。就在这时,华黎也慢悠悠地走了上来。
她看了一眼地上的旺财,故作高深地叹了口气。黑狗能辟邪,如今连黑狗都死了,
可见这里的煞气,不是一般的凶。她转向我,脸上带着一丝悲悯。
只有把别墅送给我这等身负功德与法力之人,才化解此等灾厄。她说得冠冕堂皇。
我的目光,却落在了她的手背上。那里有排清晰的牙印,我认得那牙印,是旺财的。
你手上的伤,是怎么来的?我冷冷地问。华黎下意识地想把手藏到身后,但已经晚了。
我一步步逼近她。那是旺财的牙印,是不是你杀了它?华黎被我问得脸色发白。但随即,
她又理直气壮起来,挺直了腰板。是又怎么样?我是为了你好!我取了它的黑狗血,
为你画符消灾祈福!你以为我愿意被它咬吗?如果这样,你刚刚为什么不说?我追问。
纪南星见状,立刻冲上来挡在我面前。还不是因为你迷信科学,我们怕你生气才没敢说!
华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!我看向纪南星,那你呢?旺财陪了我们那么久,
你怎么下得了手?他眼神闪烁,不是我动的手!我……我也是为了你,
才忍痛割爱的!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,仿佛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,胸口剧烈起伏着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心思,都给我滚!
我在阁楼里陪了旺财很久,才缓缓起身下楼。华黎就堵在楼梯的转角处,
一脸得意地看着我。纪南星已经答应我了,这栋别墅迟早是我的。她轻笑一声,
充满了炫耀的意味。对了,南星早上骗了你,旺财是我们一起杀的。南星叫它的时候,
它还特别亲热地凑过去,拿头蹭他的腿。我一棍子下去的时候,它叫得可惨了,
却还一直冲南星摇尾巴,真贱啊。她欣赏着我惨白的脸色,得意地笑出了声。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耳边只剩下嗡嗡的鸣响。啪!我用尽全身力气,
一个耳光狠狠甩在她脸上。华黎被打得偏过头去,捂着脸,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
我反手又是一个耳光。你敢打我?她尖叫起来,你信不信我让南星跟你离婚!
我笑了,事到如今,她居然还以为我会在意纪南星。我将她死死按在墙上,
耳光像雨点一样落下。你以为我还会在意一个虐待动物的烂货吗?你这个恶毒的女人,
居然敢对我的旺财下手!……我每说一句,就扇她一个耳光。华黎彻底被打蒙了,
只知道哭喊。最后,她挣脱我的手,连滚带爬地跑了。3没过多久,
纪南星就带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华黎踹开了我的房门。他指着我的鼻子骂,你怎么这么狠毒!
华黎躲在他身后,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,脸上还带着清晰的巴掌印。南星,
你别这样对她……她拉着纪南星的胳膊,声音哽咽,都是我的错,
我不该多管闲事……纪南星回头,心疼地看着她。你没错!错的是她!他又转向我,
眼神里满是厌恶和失望。华黎看在我的面子上,好心好意帮你,劝你把房子过户给她消灾。
你不接受就算了,还动手打人?我平静地看着他们,只觉得滑稽。纪南星,
我们离婚吧。纪南星怔住了。华黎也愣了一下,随即好像抓住了什么证据,你看,
我就说这别墅风水不好,已经影响到你们的婚姻了。纪南星回过神来,眉头紧锁。林晚,
你还是及时止损,把房子给华黎吧!别闹脾气了!华黎被你打成这样,
还一心想着为你好,你就不能懂点事吗?我的怒火再次被点燃。懂事?
懂事就是要把我的房子拱手相让?懂事就是要眼睁睁看着你们合伙杀掉我的狗,
还要感谢你们为我好?纪南星,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?我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
华黎在一旁状似好心地劝着,趁着混乱,她的手却猛地一扯。我左耳上戴着的耳环,
被她一把扯掉了。耳垂被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,鲜血立刻涌了出来,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流。
人血!华黎看到血,旋即双眼一翻,晕在了纪南星怀里。纪南星立刻抱住她,满脸紧张。
他看都没看我一眼,小心翼翼地抱着晕倒的华黎,将她送去了客房。我站在原地,
血滴落在地板上。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,我手指上长了一根倒刺,
他拿着指甲剪小心翼翼地帮我剪掉,生怕弄疼我一丝一毫。而现在,我的耳朵被扯裂,
鲜血淋漓,他却只顾着他那晕血的青梅。那一刻,我对纪南星彻底心死。
4我喊来家庭医生帮我处理耳朵上的伤口。医生手脚很麻利,不一会儿,
偌大的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关上门,疲惫地躺在床上,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不知过了多久,我惊醒,发现晚上长亮的灯居然灭了。窗外电闪雷鸣,我吓得把被子蒙过头。
我从小就怕黑,更怕停电的雷雨天。就在这时,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像是女人的哭泣声,
近得仿佛就在我的床边。我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突然,
有人用棍子狠狠地打在了我被子上。隔着厚厚的被子,那力道依然打得我浑身生疼。
我尖叫着想要掀开被子,却被人死死按住。棍子一下下地落在我身上,背上,腿上。挣扎中,
我的头部被狠狠地打了一下。我左耳的伤口似乎又裂开了,脑袋一阵剧痛。我放弃了挣扎。
这时,头顶响起了华黎和纪南星的谈话声。华黎的声音里带着怨毒和快意,
总算出了口恶气!看她还敢不敢打我!纪南星松开按着我的手,得意洋洋地说,这下,
她肯定会把房子转给你了。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停电的雷雨天。小时候下暴雨,
她那不靠谱的爸妈把她一个人忘在停电的幼儿园。这阴影,她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听到这些话,我气急晕了过去。第二天,我是在一阵阵酸痛中醒来的。我挣扎着坐起来,
感觉全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。我平静地拿起手机,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。妈,来接我。
我眼神坚定,心下已经活络了起来。想要我的房子,做梦吧。当我提着包下楼时,
纪南星和华黎正坐在客厅里喝咖啡。纪南星见我浑身是伤,他扶住我的胳膊,语重心长地说。
你看,我就说这房子不干净。你要去你母亲那儿住吗,也好,这里不能再住了。
房子的手续,你尽快抽空办一下,转给华黎,我们大家都安心。我没有搭理他,
甚至没有看他一眼。他却当我是默认了,看向我的眼神势在必得。我坐上母亲派来接我的车,
绝尘而去。我走后当天晚上,纪南星和华黎以为大局已定,开开心心地出去喝酒庆祝。
他们喝到了天亮,才醉醺醺地打车回家。当看到那一堆废墟时,两个人全都愣在了原地。
5我的别墅……我的别墅……怎么会这样……华黎瘫软在纪南星身边,嘴里反复念叨着。
纪南星则握着手机,死死地盯着那片废墟,眼睛瞪得仿佛要从眼眶里掉出来。不远处,
一台巨大的挖掘机正停在瓦砾堆旁,几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指挥现场。
一个看起来像工头的中年男人,正拿着图纸和身边的人说着什么。纪南星疯了一样冲了过去,
谁让你们拆的!他一把抢过工头手里的图纸,愤怒地撕扯着。这是我的房子!
你们凭什么拆我的房子!工头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愣,随即皱起了眉头。
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纪南星,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你谁啊?我是这房子的主人!
我叫纪南星!他声嘶力竭地吼道。工头掏了掏耳朵,从口袋里摸出一份合同。
房主不是叫这个名儿啊。他把合同拍了拍,指着上面的签名。房主叫林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