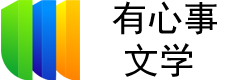陆家有两个儿子,大儿陆长洲因病常年在云霞山养着,她嫁进陆家两年,还不曾见过他。
陆长盛是老二,他身姿修长,面容俊朗,惯爱穿白衣,儒雅清贵,实在不像曾在战场上厮杀的武夫。
而她是安北侯独女,因父亲功勋卓著,被封为郡主。
五年前父亲牺牲,母亲又一病不起,不久病逝。
她为父母亲守孝满三年后进京,由皇上赐婚,嫁进陆家,以完成两家在她和陆长盛年幼时订下的婚约。
她嫁进陆家时,陆尚书已经过世,陆家凭着他的余荫在盛京勉强站住脚。
说来,她算是下嫁。
因此,她在坐下以后只向坐在正位的陆老夫人点了点头,以示尊敬。
而坐在她对面的元氏,还要起身向她行礼。
不过她这个礼却行的心不甘情不愿,甚至还带着火气,草草屈了屈膝就又坐下了。
“轻芷考虑周全,过年就该一家人团团圆圆的。
”陆老夫人笑着点头道。
陆老夫人也就五十来岁,但头发已经花白,脸上皱纹也很深。
陆尚书过世后,陆家生计艰难,她累身累心,一下老了十多岁。
直到她嫁进陆家,带着丰厚的嫁妆,又为陆长盛谋取了一官半职,陆家日子才好过起来。
阮轻芷应和笑着,并不主动提其他的事。
陆老夫人笑容先淡了,继而长长叹了口气,道:“咱们陆家不说簪缨世家,也算书香门第,家风蔚然,怎么就摊上这样的事了。
”说着,陆老夫人用手拍了拍桌子,一副气愤难平的样子。
阮轻芷转头看了陆长盛一眼,他此时低着头,一脸的羞愤。
“这韩寺卿,我接触过,是个贤明清贵的好官,他夫人听闻也是知书达理之人。
”言下之意,人家清清白白的怎会胡乱冤枉人?“弟妹这话什么意思,莫非是以为老二有这本事?还是说他将这本事在你身上使过?”元氏突然瞪着眼睛冲阮轻芷喊了这么一句。
阮轻芷脸色一沉,“大嫂,有些话说出口前最好先过过脑子!”“不要以为你是郡主就目中无人,你……”“行了,先说眼前的事吧。
”陆老夫人瞪了元氏一眼,缓了一缓后,再看向阮轻芷道:“那韩夫人非说老二强辱了她,这不血口喷人么!老二品性如何,你是最清楚的,且不提这个,他……”陆老夫人话没说透,阮轻芷怎会不明白。
元氏的话不中听,但却也倒出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陆长盛根本没有这本事。
他前些年上战场伤了根基,根本无法行房。
而她和他成亲三年,他甚至都没有摸过她的床!一个下面不中用的男人,如何强辱一个女人?但这事却不好明说,毕竟陆长盛一个大男人还要脸面。
从喜瑞堂出来,外面雪又下大了。
陆长盛给她撑着伞,夫妻二人并肩走,一路无言。
直走到廊子上,陆长盛突然转身将伞递给霞月,而后拉着阮轻芷躲进廊庑下。
阮轻芷正要开口,他一把抱住了她。
抱得紧紧的,脸用力贴着她的脸,亲昵的仿佛要将她融进他身体里。
“你……”他捂住她的嘴,将她抵到墙上,额头抵着她的额头,呼吸粗而急。
阮轻芷看到了他眼里的渴望。
她知道他想,但……他的手握着她的腰肢,力道很重,摩挲的两三下后,猛地扯开她衣襟。
“别,别……”她的呼吸也乱了。
这时,他身子却一颤,再看向她时,眼里只剩挣扎和无力,他红着眼将头偏过去,倚着她肩膀。